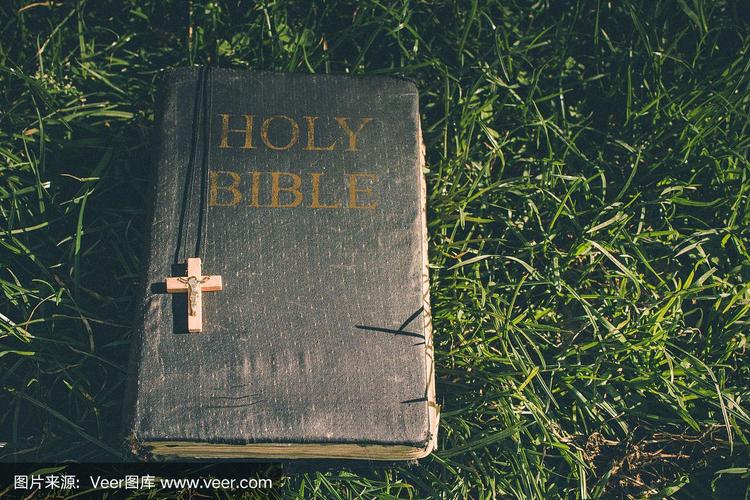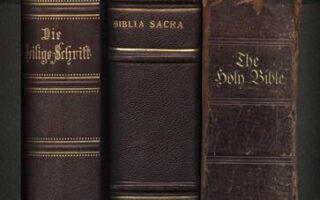文/马可·汤普森(Mark D. Thompson)译/述宁校/李亮雅斤
毋庸置疑,马丁•路德对圣经的研究是推动在十六世纪欧洲教会颠覆性的宗教改革之关键。路德是当时基督教思想改革的核心人物,而他本人更是一位圣经学者和传道人。从1513年一直到1546年去世,他一直在维腾堡大学及其邻近的城堡教堂(Schloßkirche)教授圣经。他写下大量的解经著作,并且这些资料多数得以存留(如下表所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如此大量的资料对于理解从其本身得出的各样结论有很大帮助。路德对圣经的本质和用途的研究分散在他33年的教学生涯中,并且是在一系列的处境中以不同形式被记录下来的。任何对路德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的努力都需要被筛选和评估;并且,它们都可能会被我们的神学关注点和当代的神学争论带来的影响所歪曲。单单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证据就表明,诠释者们很难忠于路德的原意。
路德对圣经明晰性的研究
当然,如果某个权威文本本身是不可理解或者意义不明的,那么诉诸这样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教会介入成为教导的权威就是正当的。这样,在路德解经生涯的开始阶段,他相当确信,圣经在被诚实地和带着信心地面对时,是明晰的。路德神学的这一因素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兴趣[12]。然而,正是路德自己的话为我们提供了他对这一基本观念的经典陈述。因为教训中存在这些因素,他于1520年被罗马教廷定罪,对此他辩护道:
要么,你能告诉我,当两个教父的观点自相矛盾的时候,以谁的为准吗?圣经应当能为此提供裁断,而且除非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将圣经放在首要位置这就不能达成,这也是教父们承认的,即圣经本身能解释自己,能证明、判断并阐明一切的事情,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明确、可知并且清楚明白。
有人暗示,在圣餐争论后期新教阵营的分裂中,路德没能坚持这一观点。但是路德自己的著作却证实与此相反。他对圣经明晰性的坚持是关于赎罪劵的辩论内容的一部分;在1525年与伊拉斯谟的辩论中,在1520年代后期与慈运理关于圣餐的辩论中,甚至在1530年代和1540年代的晚期解经作品中,他都如此宣称。如果圣经不具备明晰性,路德诉诸圣经权威性的做法就几近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说纵贯路德的整个教导生涯,这个观点在其思想中举足轻重。
事实上,在与伊拉斯谟就人类意志的状态及其在救恩中的角色的辩论中,路德诉诸圣经的双重明晰性。在给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的答复的开篇,路德总结性地阐明了他的这一观点:“简单来说,圣经的明晰性和它的晦涩性都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在地牵涉到话语事工;另一方面则关乎心灵的理解。”路德认为,这两个维度严格来讲都并非天然的、一段话语或者人类的理解力本有的内在性质。它们都是神之灵的工作。外在的明晰性必然是因神出于恩慈选择人类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他自己而赋予的。圣经文本的语汇并不是无限可塑的,正如路德后来所说的——甚至一个异教徒、一个犹太人或者一个土耳其人都能正确解释任何特定经文的含义。内在的明晰性也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必须的,因为因罪而黑暗的心阻挡人的理解,即使他能把整本圣经背下来。
正是在主张圣经明晰性的背景下,我们发现了“圣经自己诠释自己”这一释经原则。路德反对中世纪的根据以往的解经家或神学家对每段经文的注释来解释圣经的做法。这种“对注释的注释”(glossing of the glosses)而非直接研究圣经文本的做法,使基督徒们失去了被神话语光照的宝贵机会。路德呼吁不是要专注于教父们的注释,而是要委身教父们研究圣经的方法,即在整本圣经的背景之中来研究经文文字本身。路德没有教导他的学生和其他人使用教父们的注释来解释难懂的段落,而是鼓励他们利用圣经的上下文,即比较“前文和后文”,特别是利用圣经里其他涉及同样问题的清楚易懂的经文来解释较难理解的经文。“必须明白,不带任何注释的圣经就是太阳和它所有的光芒,是所有教授圣经的人得到光照的来源,而不是反过来。”对于自己的解经工作,他也坚持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我不想因为被看做是比众人都博学而受尊崇,唯独圣经本身才是支配性的:通过圣经和神自己的灵来明白圣经,而不是借助我的心灵或是其他人的心灵。”
基督原则
在路德的圣经研究中,另一持续出现并明显的要点是,他坚持整本圣经的核心在于见证基督,当然这一点在中世纪神学处境中并非特例。“基督的原则”是解经传统中的共同财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路德在准备他第一个关于诗篇的系列讲座时,就参考过雅克·勒菲弗·戴塔普勒(Faber Stapulensis)在1509年出版的注释,戴塔普勒坚持诠释圣经的基督中心论。但是路德在应用这一原则的时候,要比他的前辈们更加严格。在他的诗篇注释的前言里,他宣告:“除非文本显然是在讲论基督以外的某个人,每个预言以及每位先知都必须被理解为是指向基督的。”随后他援引了约翰福音5:39,这也表明路德确信这样的原则实际上是圣经本身所指示的。此外,在这些讲座的第二篇前言里,路德斥责“那些以属血气的方式理解诗篇的人,比如犹太人,他们经常将诗篇应用于某段与基督毫不相干的古代历史”。
这个“基督中心论”并不是路德作为解经家的成长历程的初级阶段。有证据表明,他从来没有违背他的信念:圣经的主要作用是让人认识基督。1522年发表的路德的一本讲道集Kirchenpostille,其中就体现了路德的信念:“整本圣经都在指向基督”。1525年,他问伊拉斯谟:“如果把基督从圣经里面拿掉,你还能找到什么呢?”1532年,他在餐桌上告诉自己的学生:“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圣经里所有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他写的。”
我们已经提到过路德的形象描绘:圣经(特别是旧约)就像是一个襁褓,里面包着基督。他甚至说:“襁褓虽是简单破旧的,但是躺在里面的基督却是至宝。”路德认为,对圣经文字、语法结构以及其他文学特点的研究是次要的,圣经研究的首要目标是认识基督,以及如何以信心回应。然而,路德的勇气不止于此,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发表了另一名为Fastenpostille的讲道集,他用寓言的形式从福音的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圣经的本质:
圣经是我们主基督所穿戴的衣服,在那里面主向我们显现,使我们可以找到他。这件衣服是上下一片织成的,是不可分割的。但是那些兵丁,就是那些异教徒和制造分裂者把这件衣服从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拿走了。他们的主要危害在于他们迷惑所有人说,整本圣经都赞同他们,符合他们的观点,从而占有这整件衣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路德的著名格言——圣经最重要的目的是“宣讲并反复教导基督”。因此,解经家的任务就是寻找那些“宣扬基督”(was Christum treibet)的内容。详细地阐释圣经(这里他主要是指旧约圣经)却不提说基督,就是在歪曲圣经的信息。路德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他把这一原则应用到正典本身,而对圣经书卷提出一些严重的质疑,比如雅各书似乎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圣经书卷应有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关注。这也是库伊曼(Kooiman)所说的路德的“宣讲性批评”(kerygmatic critism)。
在路德为1535年的辩论所准备的一系列注释中,有关于这点的论述,被人经常引述:
49. 因此,如果那些敌对者借用圣经反对基督,我们就请求基督来反对圣经。
50. 我们有主,而他们有的只是仆人;我们有基督为头,而他们只有脚或其他肢体部分,而相对于它们,头理应有优先权和统治权。
路德在此的关注点,尤其是从上下文来看,并不是要削弱圣经的权威性。相反,他如此彻底地相信整本圣经都是见证基督和他所成就的救恩,以至于他完全拒绝容忍任何导出另外意思的圣经解释,因为这样的诠释忽略了圣经的本质和目的。后来的人们无法接受这样一种用圣经的所有内容来宣讲基督的执着方式,也不能接受按他所要求的那样自始至终地应用同一原则。但不管怎么样,路德强调圣经明确地见证基督和在他里面所成就的救赎。路德对圣经整体性的态度是他在圣经诠释的历史中所做贡献的核心部分,这一点没有人会真的质疑。
在圣灵中读
综上所述,如果把对圣经的研究当成纯学术工作,把应用律法-福音的解经法或者类似的方法当成是纯粹动脑子来抠细节,就是对路德的误解。在路德看来,读经和听道从来都不全是甚至根本就不是学术活动,而是宗教信仰活动,实际上是整个信仰生活的缩影。正如路德在1519年的第二次诗篇系列讲座中所说的那句著名的话:“不是理解、阅读、推理造就神学家,而是如何生,不,是死和被诅咒造就了一个神学家。”然而,这都是在神的话语面前的生、死和被咒诅。在路德1539年版本的德语著作里,这一观点已经清楚出现了:路德试图通过诗篇119篇提供的三个原则——祷告(oratio)、默想(meditation)、灵性挣扎(tentatio)——来为“正确的神学研究方法”提供一个指导方针。其中的Anfechtung(tentatio的另一个表达)指的是一种经验性的现实,这是路德为不同语言的神学词汇作出的一个持久贡献。正是这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一激烈挣扎的维度——在神启示他自己的光照中人的煎熬——被路德看为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块试金石,不仅教你认识和明白神的话,更是让你经历神的话是多么正确、真实、甘甜、美好,又是多么充满能力与安慰人心,神的话是在所有智慧之上的智慧!
对路德而言,释经的有效性与释经的正确性有关,并且这种正确性不是简单体现在精确地解读文本上,而在于人在这位借助文本向人说话的神面前,认出自己的位置。正如路德在他的生涯初期所说的,“有很多人能很智慧地进行推理,但是如果人不敬畏神,他读经时就没有智慧,就不能读懂圣经。而一个人越是敬畏神,就会越明白圣经。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不仅仅是谦卑的神学,更是一种认识:在诠释的任务中存在着属灵的维度,它不能被简化成为人的聪明。1518年,在给朋友乔治·斯帕拉丁(Georg Spalatin)的信中,路德写道:
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想读懂圣经,靠学习或天生的聪明是没用的。所以你的首要任务是祷告,你必须祈求神大大怜悯你,让你能真正明白他话语的意思,并通过话语在你身上的成就来讨他喜悦,是为他自己荣耀的缘故,而不是为了你或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荣耀。因为除了它们(圣经)的作者,没有人能教授这些圣洁的话语,正如他(主)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约6:45;赛54:13)”。因此,你必须首先否认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单单依靠圣灵的浇灌。相信我,因为我之前在这方面已经有过经历了。
很明显,这和与伯纳德(Bernand of Clairvaux)相关的谦卑神学,以及中世纪后期德国神秘主义中的某些内容,有着一种深深的共鸣。但是,这一信念的根源远比这些更深刻,源于有着悠久历史的“圣言阅读”(lectio divina,sacred reading),后者被巴黎的圣维克多修道院(Abby ofSt.Victor)的学者们用于圣经的学术研究。对圣经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人委身基督的一部分,并且不能与他在神面前的全部生活分开。解经者首先也最重要的(身份)是站在他的创造主、救赎者和审判官面前的一个被赦免的罪人。
向特定对象宣讲的话语
路德在解经贡献上的最后一个特色常常被人忽略。终其一生,路德都认为,神的话不仅仅是被写下来和被阅读的,而是必须被宣讲并被听见的。圣经有个特别的本质,它是应该让人听的,这和永生神与他百姓关系之本质有关,新约本质上尤其如此。路德认为新约首先不是一个文本,而是讲道。路德在1526年关于玛拉基书2:7的一次讲座中大胆说道:
这是一段针对藐视神的言说之人的经文。嘴唇是教会的公共水库,唯独在这里面保存着神的话。你看,除非这些话被公开地宣讲,不然它们就消失了。这些话被宣讲得越多,被保留得就越多。阅读它们没有听它们的果效好;真实的声音能教导、劝勉、辩护以及抵挡错谬的灵。对于被写下来的圣言,撒但一点也不在意;但是一听到被宣讲的圣言,他就逃之夭夭。你看吧,它们能穿透人心,领回那些失迷的人。
除了话语宣讲出来的果效,以及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听道本身作为灵修方法的组成部分,在此还有路德所关注的更重大的神学议题。他坚持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形态是由神所选择的与人相交的方式决定的。在基督再临之前,神没有让自己直接被人看到,作为“隐藏的神”(Deus absconditus)他通过话语而非形像向我们显现。因此,成为基督的门徒就是需要听他的话,并且相信他的应许,而不是直接眼见到神的形像。路德确实常常强调说:“只有耳朵才是基督徒们的器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路德强调听过于读。他坚持认为“话语本来就该被聆听”。重要的是,这也导致路德看重讲道过于写作;他的警句就是:“教会不是拿笔的地方,而是开口的地方。”在他关于诗篇的第二次系列讲座中,路德解释说:“在教会,仅仅读书和写书是不够的,说和听至关重要。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希望教会有更多的好布道家而不是好作家。”
但是,好的讲道必须基于对圣经文本的仔细研读;特别是,要注意如何向当代的会众讲圣经里为他们所说的话语。路德的讲座和注释显示出他对圣经的当代性的关注程度;这种意识在最近的路德研究中得到了强调。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并非在阅读一个只是详细记录了神在古时的作为的古代文本。就像他在早期的加拉太书注释中所写的那样:
如果圣经只是被用来了解过去而跟我们自己当下的生活方式无关,它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话,它就是冰冷的、死的,甚至根本不是神圣的。但是你看,对我们现在的时代而言,这些经文是多么合适、生动和必要啊!
然而,将圣经经文随意地应用到当下的问题和境况,与只把圣经看做古籍同样有害无益。因此,路德试图在他的学生和读者身上培养一种能力,以辨识圣经中的哪些话正是对他们说的。出于此负担,他在出埃及记布道中加入附注“基督徒当怎样看待摩西?”(1525年):
我们必须清洁地面对圣经。从一开始,神的话就是以各种方式临到我们。仅仅确认这是否是神的话和神是否说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清,神是在对谁说话,他的话语是否对我们适用。它们的区别重大,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神曾对大卫说过,“从你的后裔中必兴起一位做王”,诸如此类。但这不是关于我的,也不是对我说的。如果神想向我说话,他就确实会向我说。你必须定睛于那些适用于你的话,它们是对你说的。
所有圣经经文都可以有机和直接地与基督联系起来,但并非所有经文都能适当地直接联系于信徒的生命。即使那些不是直接针对我们写的部分也会对我们有益处,尤其是它们能向我们阐明基督其人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然而,要想避免像狂热分子那样异想天开和危险地歪曲圣经教导,就要仔细考察文本的上下文,探寻与目标会众相关的线索。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路德因为强调神话语的当下时代性、有力和有效性,甚至常常违背了自己的一些理论。然而,在上下文中寻找意义这一原则中,像在其他许多原则中一样,路德预先触及了现代释经学的一个重点关切。
路德的贡献
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出现的“路德热”有目共睹,对路德生平和作品的研究层出不穷。在所有这些著述里面,受到持续关注的是他对圣经的态度,特别是他的解经和释经原则。人们开始认真对待路德自己的宣告,并说他仅仅是一个传讲话语的传道者,而其他的都是从他对圣经的委身里来的。通过对他与教父以及与中世纪的解经传统之间关联的细致研究,人们发现了一个理解他作品的新视角,这也揭示出早先人们把他当做是“从无到有”(ex nihilo)地建立新教圣经研究方式的英雄来推崇,是有问题的。这也证实了,他正是在与传统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了真正的创新。在最近几年中,人们越来越多地探索和评估路德在释经术语方面的贡献,而不是把后世形成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哲学视角这些释经基本原则强加在他身上。在这方面的很多领域中,研究路德的学者可能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很少有人怀疑在与路德“对话”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价值。从这位十六世纪维腾堡的圣经学者身上,当代释经者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他们很容易看到前人的文化背景如何扭曲了他们的释经努力,却很难看到自己身上存在同样的问题。
对路德的圣经诠释原则的过分系统化而造成的危险,已经有人提出了恰当的警告。对一般性的释义学以及圣经释经学的集中研究(尤其是二十世纪最后25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确性和复杂性,甚至是抽象性;如果要在这位十六世纪解经家的著作中找到这些,那就是搞错时间了。说到此,毫无疑问的是,路德对后世探索圣经诠释的影响意义巨大。中世纪的解经方法被淘汰,路德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放弃在经文里寻找属灵含义的解经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从简单的语法意义以及圣经文本的上下文处境来研究神学意义。他恢复了“圣经的明晰性”(claritas Scripturae,the clarity of Scripture)这一原则的经典表述,并将这原则的含义朝向极其挑战人的方向发展。他重申并赋予基督中心论的圣经研究一个更可靠的神学根基,就是以律法和福音为推动力,并因此使圣经真理直接对基督信徒生命造成冲击。他敏锐地关注圣经里每一个应许、劝诫、命令和警告里有关基督的表述,也以此来规范对经文本身的诠释和应用。最后,路德的这些新发现是源于他明确地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中的最终权威,并且这些新发现反过来也进一步坚固了他的这个确信。
作者简介:
马可·汤普森(Mark D.Thompson)是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摩尔神学院(MooreTheological College)神学、哲学和伦理学系主任,2013年起担任该神学院院长。他的关于路德的圣经教义的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为专著 《站在稳固的根基》(A SureGround on Which to Stand)。他曾与人联合编辑《传给万国的福音》(The Gospel to the Nations)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