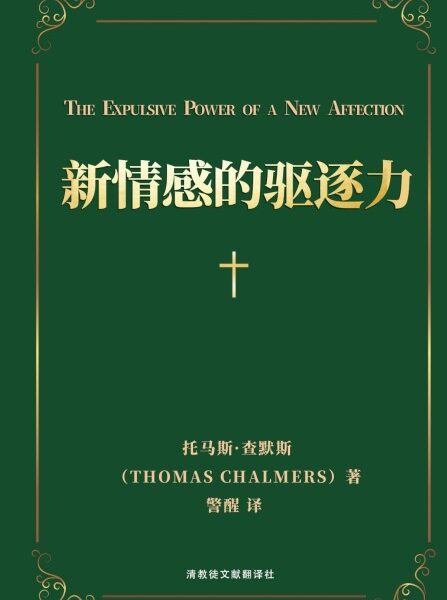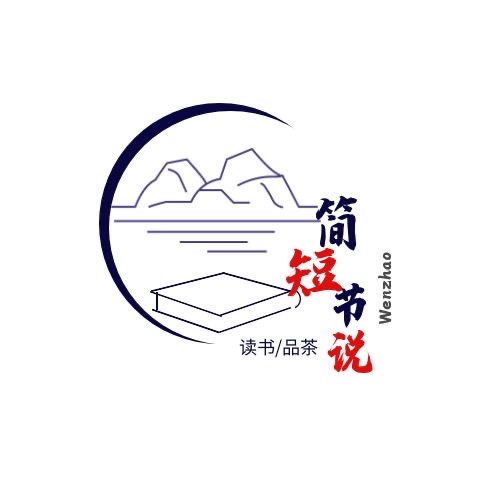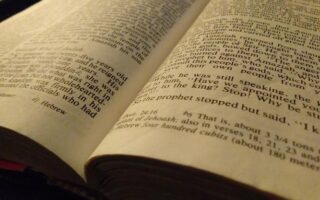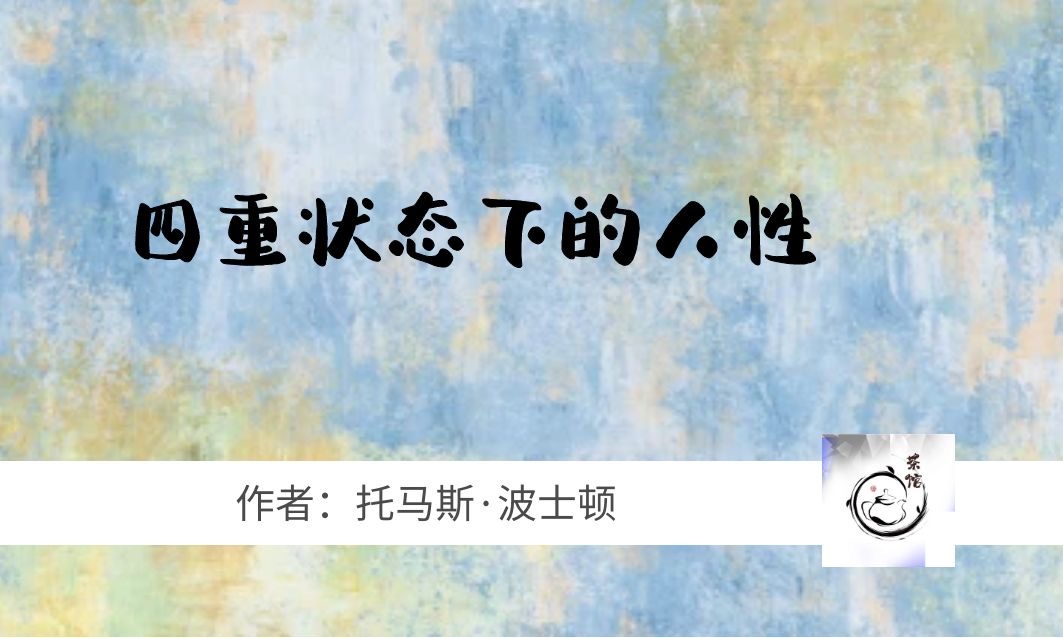文/托马斯·查默斯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一一约翰一书2:15
实践伦理学家试图移除人心对世界的爱,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展示世界的虚空,从而说服心灵收回注意力,使之不再关注一个不值得关注的事物;其二,是提出另一个更值得心灵依恋的对象,甚至是神,以至于心灵被说服,不再顺从旧爱,旧爱不再得到接续,而是被全新的爱所替代.
我的目的是要说明,从我们本性的构造而言,前一种方法是徒劳无功,只有后一种方法能将我们的心从辖制它的错误情感中拯救出来。完成这一目标之后,我会尝试提出一些实际的建议:爱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如果人所爱的对象身处远处,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渴求的爱。
第二,如果人已经拥有了爱的对象,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享受的爱。
在渴望的驱使下,人会感到自己被催逼走上某些道路,或是被驱赶去寻求那些满足自己渴望的活动。此时,人的心智官能就会被调动起来,开始不停地忙碌。在一个重大无比、吸引人心的志趣的指引下,他的注意力会从诸多令人分心的遐想中被唤醒,他的体力也会从原本使他枯竭的懒散中被召回;他的时间被热切和野心占满了,如果没有某些让他热切投入的目标,这些时间本会在疲倦和厌烦中消耗殆尽。虽然盼望未必总是激发活力,成功也并非总为勤勉的事业加冕;在他无常的境遇和偶尔的沮丧中,即使有偶尔交替出现的失望,他全人的机制仍会持续且和谐地运转,使他持续处在意气风发的状态和情绪中。
至此,假如根除激发这一切运转的那个渴望,这一机制就会随之停止运转,如果没有另一个渴望来代替它的位置,人就会随着他的一切本性,在一种十分痛苦和失常的被遗弃状态中行动。当他从疲劳中得到充分休息,或从痛苦中得到彻底释放后,他仍然拥有力量,这力量却不能活跃:他仍有渴求的能力,却再无渴求之物:他身上还有多余的精力,却无物与之相配,却没有任何刺激可以调动这些精力。如此,一个敏感的人就会遭受极大的痛苦,处于暴躁当中.
这种痛苦的状态常见于那些从生意场上退出、从法律行业退下来、或者是那些从逐利职业、从赌桌上退下来之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的本性需要一个可以追求的对象,先前任何成功的积累都无法熄灭这种追求。因此,最富有的商人,最英勇的将军,最幸运的赌徒,一旦他们结束各自劳力的职业,其他人常常会发现,他们虽然得到了一切,却总是萎靡不振,仿佛离开了他们至亲至乐之物。对于人类来说,如果尝试剥夺这种他们从事某种活动的固有渴望,却不提供其他的来替代,那么这种尝试将是徒劳的。他全部的内心和习性都会奋起反抗这样的尝试。一些无所事事的妇女,每晚花费数小时在赌博上,她们和你一样,深知自己所获得的金钱或胜利都不过是虚空。但向她证实这事的虚空,并不足以让她离开这既可爱又悦人的消遣活动。她无法改变习惯,因为改掉习惯后,就只剩下消极而无聊的空白。然而,这习惯却可以被另一个习惯或活动取代,因为可以有某种新的情感约束她。比如说,某个夜晚,原本安排好用来赢钱的时间,她可能宁愿暂停一次,因为接下来她需要准备参加社交活动。只有第二种情感的支配力量,才能使她做出改变;而不论怎样强有力地向她展示第一种情感的愚昧和虚空,都不能产生这样的果效.
对于这个巨大的世界而言,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单靠证明世界的虚空,以此来让世人终止他们的首要追求。想要用任何方法阻止其中的任何一种追求,这都是徒然的,除非能用另一种追求来替代。属世之人一心一意忙于自己的目标,我们若要帮助他停下脚步,需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他所追求对象本身的魅力,我们还需要考虑他在从事这一切时所感受到的快乐。因此,我们用道德的准则、雄辩的说辞,强有力地展示世界的虚空,试图以此来驱散其魅力,这恐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让他心灵的眼睛看见另一个目标,其吸引力必须足以让他摆脱第一个目标的影响,并让他从事另一种同样充满兴趣、期待和快乐的活动,就像从前一样。
正是因此,所有宣告这世界虚空的道德和悲情的说辞,都是一无所成。一个人不会因为目标的微不足道而甘愿忍受没有目标的痛苦,也不会因为所追求之物轻如鸿毛而变得没有追求,即便只是短暂的折磨,他也不会甘心承受。如果人完全没有渴望和动力,就会陷入暴躁和不安的状态中;因此,单单推毁现有的渴望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是要用另一个渴望来取代原有的渴望和习性.让一个人的心思从一个目标挪开的最有效方法,并非使之转向荒无人烟的虚空,而是要向它呈现另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目标.
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尚未得到对象之渴求状态下的爱。也同样适用于享受状态,或已经得到目标之满足状态下的爱.我们的品味很少通过自然的过程而消亡.至少它很少通过理性推理而消亡。或许它会因过度姑息纵容而消亡,但单凭意志肯定做不到这一点。然而,这些无法被摧毁之物却可以被驱逐,一种品味可能会给另一种品味让路,其统治心灵情感的权势也可能会彻底丧失。
因此,男孩后来不再是贪食的奴隶,这是因为另一更成人化的品位占据了上风,让他从前的喜好变得次要:那年轻人不再崇拜欢愉,因为财富的偶像越发强大,开始支配他:甚至有一天,对金钱的热爱也不再能拿控一个雄心勃勃的公民,因为他的内心已经陷入社会政治的旋涡之中,另一种爱在他的道德观中发挥作用,现在对权力的爱主宰了他。在所有这些转变中,心灵从来未失去过对象。对一个特定对象的爱可能被征服;但对于下一个对象而言,心灵的欲望却并未被征服。它依恋它所爱的对象,强行将其分开,不能让它心甘情愿地放弃。只有藉着更强大、更震撼的事物吸引它,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人心抓取的倾向,人心一定要抓住什么东西一一而如果这个东西被夺去,却没有其他东西代替,就会留下空缺和虚空,这对心灵的痛苦,就如饥饿对于身体的痛苦。心灵或许会被夺走某个目标,甚至多个目标,但它不会荒凉到一无所依.一颗活泼和敏锐的心是甚好的,然而它周围若没有投其所好的事物,那它只能活在自我意识的重压之下,在毫无喜乐、倍感遗弃的状态中度日如年。对这颗心的主人来说,无论他是生活在一个快乐美好的世界中,还是被遗弃到一个与世隔绝的郊外,这都与生活在黑暗和虚空中没有区别。心灵必须有所依附一并且它绝对不会自愿脱离所爱之物,也永远不会走到没有对象供它恋慕和求索的地步。
内心对本应给其带来享受的一切事物完全失去了兴趣,这种痛苦在那些过度放纵的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曾经经历各种各样极其强烈的快感,最终失去了一切感觉的能力。无聊的疾病在法国的都市里更常见,在那里,上流社会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娱乐。和英国的都市不同,法国的都市拥有多样化的商业资源和政治资源,这也让心灵的渴望越发多样化。有些人追求时尚,最终却成为了过度迷恋时尚的牺牲品,过度享受浇灭了他们享受的能力:那些原本可以享受艺术和自然之美的人,如今再看到周围的一切,只会感到索然无味;曾经在感官上享受奢华的人已然倦怠,无法再拥有更高层次的快乐。一切美好似乎都走到了尽头,就像年迈的所罗门王一样,感叹万物虚空、令人厌烦。内心经历过荒芜的人都可证明,如果一个人心中所爱之物被移除,并且没有新的事物替代,那就必然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倦怠感。人变得悲惨未必需要经历某些具体的痛苦,对万事感到厌烦,就足以做到这一点一-在精神病院里,人的感知官能和智力官能都已受损:在这种既不吵闹、也无怒吼的病房里,我们却能遇见遭遇心理折磨最高峰的人。而那个最悲惨的人,放眼广阔的自然和社会,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他驻足观看:对这样的人而言,天上地下的任何事物都失去了魅力,也不能激发他的渴望,或者让他做出回应的动作;世界在他眼中是个空无一物的巨大废墟,那里只有他自我意识的重压,没有任何能滋养他的东西,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死寂的,他只能活在自己迟钝而无用之存在的重担下.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一旦试图消灭心灵所爱之物,心灵就会如此顽强地守护它。壮士或许会被迫把自己的家让给另一个人,但另一个人必须要比他更强壮,有足够的力量夺走他的房子并取代他,否则他就一定会守护自己的住所。心灵会起来反抗自己的虚空,它无法忍受荒芜乏味的状态。试图使用这样一种剥离进程来对付内心的伦理学家,必定会被内心自身的反弹机制所挫败.你们都听过“大自然憎恶真空”的说法,至少心灵的本性亦是如此,即便心房可能更换住客,然而心房一旦变得空无一物,就要承受难以忍受的苦楚。因此,单单指出现有之爱的愚昧是远远不够的。有力动人的论证也不足以弥补心灵对象的空缺。甚至仅仅把放纵与将来审判的威胁联系起来,也是不够的。心灵仍然会抵挡所有要求,因为一旦服从了这些要求,就会导致心灵与它的一切欲望争战,从而堕入全然虚空的状态。因此,要把情感从心中剥离出来,让心灵脱离它所看重和喜爱的一切,这是一件艰难而无望的工作。而且看来,似乎唯一有力的剥离手段,就是让另一种情感主宰心灵.
据我们所知,没有哪处比使徒的这节经文有对自然情感更严厉的禁令了。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尚未经历重生的巨大而提升的影响,就要求他从世上一切事物上收回自己的爱,那无异于要求他放弃心中的一切情感。世界对旧人来说,就是一切。他的一切喜好和渴望的指向,都不会超出肉眼所及之处。世界之上,他别无所爱;世界之外,他毫不关心;要他不再爱这个世界,就等于把他心中的一切都驱逐出去.要体会放弃世界对他而言是多么重大和艰难的决定,我们只需想一想,要说服他不爱钱财(这不过世上万物中的一样),就像说服他放火烧毁自己的财产一样困难重重。如果他看到,唯有如此行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得救,他可能会在极度痛苦中不情不愿地做这件事,但是,如果他看到废墟之上有价值十倍的新的财产,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件事.
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被取代。更是另一种情感压倒了一种情感。如果不用任何爱来取代,而是直接把他心中对世间万物的爱全部剥夺,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反人性的暴力过程,等同于摧毁了他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却不给他任何补偿。因此,如果不爱世界,对一个人的基督信仰而言必不可少,那么用“旧人钉十字架”(罗6:6)的用语来描绘他生命历程上的巨大转变,就并非过于强烈,的确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至此,希望你已经明白,单纯展示世界的虚空是不起作用的。这样做的唯一作用,如果有的话,就是让心灵落入一种不可忍受的状态,即仅仅是一种赤裸和负面的状态。你也许还记得,你的心常常怀着这种喜爱和坚韧去追求,然而就在昨天,你还在为这种完全的轻浮叹息和哭泣。也许在安息日,你们在数算自己日子的短暂时,能在自己理性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当传道者把你们带到死亡之床前,对你们一切属世的追求发出责备时,当他在你面前描绘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坟墓终将吞噬一切,世上一切喜悦和乐趣即刻就被人遗忘时,你们会被他的论证触动,感到事情很严重,仿佛刹那问看见自己将要永远脱离这一切虚空的情景。
然而,一到第二天,世界的事务、世界的目标和世界的动力再次接踵而至一一因着人心的机能,它必须抓住什么,或者必须依附什么,仿佛是一种道德的必需一再次将人带回到之前的活动里;并且完全排斥这样一个喜悦和渴求都被冻结的状态,反而更能感受之前渴求状态中的温暖和能力。假如在一个人整个的生话和经历中,我们都不能看到有新生的样式,那么对他而言,教会就不是叫人顺服的学校,而只是一个供他闲逛的去处;有些讲道似乎也大有能力,可以吸引大批听众,可以使听众安静肃穆,讲道内容也充满活力,能唤起人的诸多想象,却不足以推毁这坚固的营垒。
仅靠证明世界毫无价值,这并不能消除人心对世界的爱。然而,难道我们不能用更有价值的事物来取而代之吗?我们无法仅仅倚靠说服,就让心灵以一个简单的顺服行动离弃世界。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说服心灵接受另一个事物,把世界从统治的宝座上拖拽下来,使之降到次要位置去吗?如果说宝座就在那里,必须要有人坐上去,而如今世界僭主拿权,非法占据了人心的宝座,不肯主动离开这个宁要僭主、不愿无君的位置。但是,难道它不应让位给那位合法的君王,即那位魅力足以征服一切,权能足以统管人类道德本性的君王吗?总而言之。如果要使心灵脱离对一个伟大且重要的对象的主动之爱,那就要让它与另一个对象紧紧地结合在主动之爱中;如此,这个方法就不是暴露前者的毫无价值,而是向理性的眼睛说明后者的宝贵和卓越,即“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仅仅抹除我们现有的全部情感,却让位置空着,那不仅会毁灭旧人,而且也不会产生新人。但是,当旧人离开却有新人进驻时,当旧情感因新情感的力量而主动让位时,当人腾空心房只为了给继任者让位时–这间心灵的房屋就无异于从前,是充满渴求、兴趣和期待的住所这一切都并没有阻碍或者违背我们情感本性的法则。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符合心灵运作机制的情况下,心灵可以经历一场伟大的道德更新.
我们相信,这一点可以解释福音在有效传讲时所产生的魅力。爱神和爱世界是两种情感,不仅彼此竞争,且是彼此敌对。两者势不两立,以致不能同住在一个人心中。我们已经说过,心灵不可能凭借其与生俱来的能力,将世界从自己里面驱逐出去,从而让自身变得荒凉。心灵的构造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要让心灵逐出一个旧的情感,唯有借助一个新情感的驱逐力。人的性情中再没有比此更大的改变了–当新约命令它,不再爱这世界!不,不再爱这世界的一切!而这世界包含了他所珍爱的一切,这个命令无异于要他自我毁灭!
但是,那个吩咐我们要做出如此巨大顺服的启示,也为我们提供了同等巨大顺服的工具。它把一种情感带到我们心门前,新的情感进来坐上了心中的宝座,先前的居民要么屈服,要么被赶走。在世界之外,启示把创造世界的神置于我们心灵的眼前,并以其独特的方式,让我们在福音中看见神,进而爱他.在福音中,并且唯独在福音中,神作为罪人信靠的对象显现;唯独在福音中,我们对他的渴望才不会因人罪的阻碍而变得冷淡;罪阻碍了一切亲近神的道路,唯独借助他所设立的中保才能就近他.福音引进了更美的指望,使我们得以亲近神–没有神,生活就毫无指望:心灵中如果没有神,就会被世界完全占据。是神,唯有在基督里被相信的神,才能驱逐坐在心中宝座上的世界。他除去了我们因违背他颁布的律法而生的恐惧,并且我们藉着他所赐予的信心,得以在耶稣基督的面容中看到了他的荣耀,又听见基督代求的声音,这向人类宣告坚定的善意,请求所有愿意的人可以归回,就能得到他完全的赦免和恩待的接纳。于是,一种超越人对世界之爱的爱,第一次在重生之人的心中产生,并最终驱逐了人对世界的爱。于是,我们从无法生发爱的奴仆之灵中被释放出来,藉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被收纳为神的儿女,儿子之灵就浇灌在我们心里一于是,心灵才被一个巨大且有力的爱支配,从而脱离了从前渴望的暴政,这也是脱离的唯一方式。从天而来启示给我们的信心,是罪人在神面前称义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达成最伟大道德和属灵成就的工具,对一个原本死在罪中之人的本性来说,这是任何其他方法无法企及的.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最有效的讲道应该是什么样的。仅仅向世人的眼睛展现世界的不完美,是不够的;仅仅向他们证明世上一切享受都转瞬即逝,也是不够的;仅仅回顾过去的经历,用你的回忆告诉你的良心,人心有多诡诈,人心所追求的一切有多虚假,仍是不够的.有许多福音的使者,并没有足够敏锐的洞察力,没有足够生动的表现力,没有足够描绘德行的才能,从而无法将当今社会的种种愚昧如实地活画在你面前。他虽然不能详尽地向人展示堕落的可见细节,但是他实际上却是除掉败坏之根的器皿。让他成为福音见证的忠实阐释者吧,虽然他没有能力描绘当今世界的特质:让他准确报告来自遥远世界的启示吧,虽然他不善于剖析心灵,没有小说家般的能力,可以生动地呈现出心灵所爱的毫无价值:让他去处理特有教义中的诸多奥秘吧,虽然最优秀的小说家曾对此极尽嘲讽。他或许无法用敏锐和讽刺的观察眼光,向听众揭示属世的渴望,但他可以使用交托给他的福音信息,挥动这唯一可以消灭这些渴望的武器。他不能像某些人那样,用术士的手,从我们本性的隐秘处,将它的弱点和潜伏的渴望展现出来。但他拥有真理,真理不论进入谁的心中,就像亚伦的杖一样,吞灭任何东西。尽管他可能没有资格描述,旧人本性和构造上中种种细微的阴影,但在他身上有更高级的力量,在这力量的影响下,旧人的爱好和倾向都将被摧毁,他最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
因此,让我们不要停止运用这唯一强大而积极的工具,来消除我们对世界的爱。让我们尝试每种合适的方法,好叫那远比世界更大之神的爱,可以进入你们的心里。为了这一目标,让我们尽可能除去那不信的帕子,因它会隐藏和遮蔽神的面容。让我们坚守神对你们情感的要求-不论心存感恩,还是心存敬畏,让我们永不停止地宣告,在神的整个奇妙经世中,他的目的就是要使罪恶的世界重新归回他自己。神就是爱,他以慈爱的形象彰显自己;就你而言,他别无所求,只是希望你以信心和悟性,心中生发对他回应的爱.
至此,让我们看看属世之人的怀疑:他将自己所依赖的世俗经验应用在基督教的崇高教义之上时–重生在他看来纯属无稽之谈–当他的内心执着于暂存的事物,并以自己在人类生活中训练有素的慧眼,看到周围的人同样固执时,因此他就宣告:无论是旧人钉十字架,还是新人复活,这一切都与所知道和所见证的人类真实本性截然相反。我想我们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坚定倚靠自己充沛的精力和与生俱来的才智,敏锐地观察着过去一周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并且在日常事务的各种情景中,注意到人心的转变,即对神有不断更新和日益增长的渴望,在随着时间逐渐死去,且被视为仅在安息日才会去想的事。因此,他们把一切精力都倾注到属世的事物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始终不改自己属世的情感、爱好和追求。即便他们想到了死亡,想到了死后另一种存在状态,这也不能使他们有重生那样彻底的改变,他们也不会有为死做准备的想法。他们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认为自己只需以某种体面和过得去的方式,可以履行与他们相关的那些义务,这就已经足够了;基于他们常常感受到的某些社会或家庭的道德准则的力量,尽管神的爱从未进入他们的心,但他们认为自己将来会从这个世界安全地进入另一个世界;虽然在这个世界,他们与神几乎毫不相干,但在那个世界,他们却想要在永恒中直接与神相处。在闲暇时刻,他们对有关光阴短暂虚空的说辞表示认可。但是他们拒绝将这些说法应用到自己的内心,也不愿意让这些应用改变内心的倾向,更不愿意尝试让自己的心在今生的好处中停下来,从而得着任何安息和更新。实际上,他们认为这种尝试完全是空中楼阁一-如我们所说,要把情感放在天上之事上,要藉着信心而行,要保守自己的心,要爱神而不要爱世界,不要凭肉体夸口,要放弃地上之事,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一-当听到这些时,他们就会带着充满世俗智慧的腔调,凭借他们熟悉的日常经验,把这一切都视为一场幻梦.
现在,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讨厌真基督教的人,他们认为基督教完全不切实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不相信基督教的要求,就在多大程度上不相信基督教的教义,两者完全一致。难怪只要他们觉得新约圣经的话语(word)不值得他们关注,他们就会觉得新约圣经所要求的工作(worh)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不论是他们还是其他人,都不可能逐出心中的旧情感,除非借助新情感的驱逐力。如果这新情感是神的爱,那么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人,都不可能自愿接受这爱,除非藉着不断对神自己的呈现,吸引罪人的心归向他。而正是他们的不信,遮蔽了他们内心对这呈现的辨识,使他们看不见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间的爱。他们看不见神向人所表现的温柔,就是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乃是为我们舍了他,将他交于死地。他们看不见代赎的全然充足,也看不见耶稣所背负的本该罪人背负的重担和忍受的痛苦。他们看不见神的圣洁和怜悯的交汇,神赦免了受造物的罪,却不能不为他们的罪做出偿还。对他们来说,一个人如何能从自然状态进入敬虔状态,这是一个谜,但他们若是相信神在肉身显现,敬虔的全部奥秘就会为他们解开。实际上,他们无法摆脱旧的情感,因为他们看不见那些能够使他们产生新情感的真理。他们就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没有稻草,却被要求做砖。他们无法爱神,因为他们缺乏唯一能在罪人心中滋养这种情感的食物。他们抵挡福音的要求,认为这些要求不切实际,他们反对福音的教义,认为这些教义无法让人信服;然而任何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有判断一切世人的特权),都能察觉这些错误的共通之处。
但是,如果谬误存在共通之处,那么与谬误相对的真理同样也有共通之处.人若相信基督教特有的教义,就容易顺从基督教特有的要求。当被要求要至爱神时,其他人可能对此感到震惊;但基督徒并不惊惶,因为神曾向他显现,赐予他平安,赦免了他的罪,赐给他与神和好的一切自由。当听说要将世界从心中驱逐出去时,这对那些没有什么来代替世界的人而言是不可能的;但这在基督徒而言,并非不可能,因为神是他满足的最真实的份。当听说不要再爱地上之事时,这对于那些心里匮乏再无可爱之物的人而言,这命令无异于要求他自我毁灭:但这对基督徒来说并不痛苦,因为他的眼睛已被打开,看见了天上的可喜爱的荣耀之物,他的灵魂在那里寻得一切爱情,找到最满足和最幸福的归宿。当被告知不要定睛在可见和暂存的事物时,对有的人而言,这等同于遮蔽他眼前一切可见的亮光,因为他们的有罪本性与永恒喜乐之间隔着一堵墙:但对于因信基督已经拆毁这墙的人,当他藉着信心看到那眼不能见、存到永远的事物时,他就会发现有光照耀在自己灵魂之上.告诉一个人要圣洁,但他与圣洁同行就意味着是与绝望同行时,他如何能做到呢?正是十字架的代赎,调和了立法者的圣洁和犯罪之人的安全,并且开了一条路,让成圣的影响可以进入罪人的心,如今神已经就近他,与他和好了,他与神的性情有份并逐渐有他的样式了。
将福音的要求和福音的教义分开,你要么得到一个不切实际的称义体系,要么得到一个贫瘠荒凉的正统观念。而将要求和教义结合在一起,基督的真门徒就能倚靠教义赐予他的力量做到那些要求。动机与行为相称,福音所要求的顺服并不超出人的能力程度,正如福音教义并不超出人的接受程度。信心的藤牌,救恩的盼望,神的道,还有真理的腰带,他已经穿上了这全副军装;人凭借这些就能赢得战斗,抵达高处,进入一个无往不利的新领域和新未来。这果效是巨大的,但与之对应的动因也同样巨大;尽管这种基督教诫命所要求的道德新生命的确十分惊人,但基督教信仰中有足够的力量使之存在并使其延续。福音的目标,既包括安抚罪人的良心,也包括洁净罪人的心;但必须注意,只要损害了其中一个,也会损害另一个。丢掉污秽情感的最好方式,就是接受清洁的情感;藉着对美善之事的爱,可以驱逐对邪恶之事的爱。
因此,福音越是白白得来的,就越能使人成圣;福音越是作为恩典的教义被人接受,人就越能体会福音是关乎敬虔的教义。这是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个奥秘,一个人接受神的供养越多,他回报的服侍就越多。人若是活在“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看”的原则下,恐惧之灵就必然会进入他的心中:律法式交易的猜忌也会赶走神人之间的一切信任:受造物竭力追求与造物主平起平坐,平等交易,实际上所追求的不过是一己之私,绝非神的荣耀:尽管他努力遵守一切律例,但顺服之灵却不在其中:他的思想并不顺服神的律法,事实上,在这种经世中,他永远不能顺服神的律法。唯有在福音中,接纳是作为礼物被赐下,无需金钱,无法标价,人在神那里的安全感才不会受到干扰,人也才能在神那里得到安息,人对神才能像一个朋友对他的朋友的信任一样,对神建立起他的白白和慷慨的认识:一方对做与另一方有益的事而感到欣喜,而另一方也才会发现,他内心最真实的快乐是在于对恩典的回应,这唤醒了他的心,使他领悟到一种全新道德生活的魅力。
倚靠恩典得救一倚靠白白的恩典得救–不是出于行为,而是在乎神的怜悯。这样的救恩,对于拯救我们脱离公义之手的审判不可或缺,对拯救我们的心脱离不敬虔的冷漠和重担更是不可或缺。福音中哪怕保留一丁点的律法主义,都会挑起人与神之间的不信任,都会抵消福音融化和赢得人心的能力。因此为了这一目的,恩典越是白白的,就越好。许多人担心,这一特定教义会成为反律法主义的开端,但实际上,这一教义是一个重生灵魂的开端,能在人心里生发一个全新的倾向,以此来对抗反律法主义。在白白恩典的光照下,伴随着福音的爱流入人心。我们何等程度损害了恩典的白白特质,我们就在何等程度上赶走了福音中的爱。当罪人相信他是因恩典得救之时,他就会在自己心中发现一种从未有过的转变道德的强大力量;以致他感到他不得不献上自己的心,弃绝不虔不敬的行为。想要最好地完成任何工作,我们就应该使用最合适的工具。
我们相信,对于那些渴望拥有文中所讲的伟大德性,却深感自身本性的倾向和渴望过于强大的人,以上这些话可为他们提供某些实际的指引。我们知道,除了让自己的心爱神之外,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驱逐我们内心对世界的爱;除了在最圣洁的信心上建立自己,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心爱神。那些反对福音见证的人,是不可能拒绝世界的:但是对于相信的人,一切皆有可能。若不藉着信心而努力,就是不使用正确工具的徒劳做工。但信心通过爱动工;因此,若要从心中驱逐违背律法之爱,就要将遵守律法之爱纳入心中。
设想一个人站在这个青翠世界的边缘,他望向世界,看到每一片田野上都充满了微笑,大地的祝福酒遍每一个家庭,美妙的阳光照耀在每栋房子上,人类情谊的喜悦点亮了许多社群。设想这是他默想的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在他居住的这个属神的星球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墨黑的幽暗和深邃的未知。那么,你认为,他会愿意告别在他眼前地上的一切光明和美丽,投身到远离这一切的可怕孤独中去吗?他愿意离开人群聚集地,成为虚无之境的孤独游荡者吗?如果宇宙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片荒野,他会因此放弃近在咫尺的、无比吸引他的生命和欢乐的家园吗?他难道不会紧紧抓住他的感官。他的生活和他社会吗?难道他不会乐意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坚实的立足点,难道他不会在宇宙的荒凉面前退缩,选择寄居在这遮盖大地的银色天幕之下吗?但是如果在他默想的时候,某片幸福的圣土飘过;那里射出超凡的荣光,传来甜美的韵律:他清楚地看到,在那里,有更纯净的美丽遍满每一片田野,更真挚的喜乐充满每一个家庭;他能看到那里有平安、敬虔和恩慈,这一切让那里的每个人心中都充满德性的喜悦,将整个社会里的人与人,以及人与神都联为一体。他还会看到,那个地方不知何为痛苦和死亡;更重要的是,那个地方欢迎他,一条新的道路已经为他打开。难道你们不知道,从前的荒原,已经成为邀请之地;而如今的世界,将成为荒原吗?
荒无人烟的世界无法做到的事情,一个充满幸福景象的世界却可以做到。人的心灵一直都倾向于近处的可见的场景,但如果有另一个人向他展现另一个世界,不论是藉着信心,还是借助其他感官,就可以在不暴力破坏其道德本性结构的情况下,使他向现今的世界死,向另一个远处更可爱的世界而活。